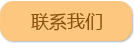戏曲时讯
-
2026-02-16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新春贺辞 -
2026-02-12
欢欢喜喜过大年|正月初三—初五 秦腔《五女拜寿》陪您过大年 -
2026-02-11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2026年春节演出安排新鲜出炉 -
2026-02-10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开展节前走访慰问送福活动
首页 >戏曲漫谈>名家评论
七十岁的青春
时间: 2009-03-31
点击量: 6957
七十岁的青春
——《春华秋实.老艺术家专场晚会》观后
我把这一场演出称作绝唱,不是说这些演唱者以后绝对不会再走上舞台,而是感觉到,要把这场演出的所有参与者,一个不缺原班人马原汁原味的集体亮相再重新复制一次,难度非常之大。这是一群七十岁左右甚至接近八十岁的秦腔表演艺术家,在一个特殊场合特殊时刻来了一次特殊艺术释放,所呈现出的特殊灿烂,对我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艺术享受,而是一次生命意义上的共振。
对于广大秦腔迷,她们的名字耳熟能详,她们所塑造的形象,早已存储于记忆深处,那是西湖寒林中无比惆怅忧伤的白素贞的仙姿,那是暗夜沉沉中悠悠飘荡的李慧娘的香魂,那是疾风暴雨中遍体鳞伤走投无路的吴清花在喷吐一腔怒火,那是狞厉阴森的刑场上控天诉地的窦娥女在发出最后的诅咒与呐喊……这样一群或仙或鬼或生或死的至真至善的青春精灵,最初总是由有着同样青春与美丽的艺术家一代一代演绎而成,艺术家留下了唯美的青春,而他们自己却渐渐老去,就如同曾经滴翠吐红的婆娑大树随着季节的风雨,千花渐落,霜叶渐染,最后隐没于冬日的雾霭之中。但突然之间,他们又像被春雷唤醒,像又一次在古老的枝头绽开新蕊一样,戴上行头,穿上剧装,一经揭开幕帘,甚或还在后台只一声叫板,就让昨日回到眼前,那一群美与善的尤物就如星辰般地倏忽闪现……不能说只有演绎青春的才拥有青春,当满头华发手持利斧的祥林嫂的扮演者一声尖板刺破长空的时候,当两鬓如霜慷慨悲壮的佘太君的扮演者用碗碗腔长调咏叹的时候,当与冤塞乾坤的儿媳相拥诀别的蔡婆婆的扮演者一段撕心裂肺的滚白,一声恸断肝肠的喝场,你就忘了这样一些艺术家竟也一个一个地步入了耄耋之年。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些艺术家还像当年一样字正腔圆,或者还像当年一样准确无误地投足出手,赵盾的扮演者已无法让嗓音抵达高位,杨侍郎的扮演者甚至跪到最后都难以顺利地站起,但这一批艺术家直到如今,极尽全力追求的就是把戏做足,做到淋漓尽致。他们在此刻所呈现出来的,虽然不是青春年华时的巅峰状态,却绝然是用所可能拥有的最后的艺术能量来完成一次生命的绽放。这种毕极生于一役的不懈追求,在我的灵魂深处发生轰鸣。表演艺术家没有作家幸运,作家没有离开舞台的失落,不论年岁如何,只要还能举得起手中的笔,他就能继续展示心灵;而表演家的限制就太多了,容貌,身段,嗓音,武功,甚至记忆力,任何一个环节发生故障,还要留在舞台上,都是难以如愿的。但是,这一批古稀之年的艺术家,居然在离开舞台多年之后又并肩携手,粉墨登场,回望了一次青春,重温了一次春梦,就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
七十岁艺术家的青春,是在他们剧院七十岁诞辰之际展现的。他们所称之为“家”的这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走过了七十年风雨历程,迎来了七十岁华诞,庆祝演出持续了百天,全方位多角度全景式立体化的展示了剧院的累累成果,最后带总结性的演出是三场晚会:先是被称作《七十年华章》的综合晚会,接着是优秀中青年艺术家大型交响音乐演唱会《盛世秦风》,压轴的就是上边讲到的老艺术家专场晚会《春华秋实》。
百场演出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文化大餐和秦腔盛宴,是一个艺术团体的豪华亮相和辉煌造型。百场演出,把七十年创造的代表剧目一网打尽,把老中青三代演员一网打尽,那些梅花奖获得者,那些国家一级演员,那些老一辈表演艺术家,那些刚刚完成学业的莘莘学员,一同出动,甚至同时出动八个王宝钏,八个桃小春,八个梁秋燕,八个王桂花,名符其实的群星灿烂,群芳竞艳,英才荟萃,五光十色,在当下冷寂的戏曲舞台上,划出了一道十分罕见的炫丽与斑斓。那些梅花奖获得者的魅力独具自不必说,那些中青年优秀演员的活力四射自不必说,更让人触动的是,这些日行中天的实力派人物,与风烛残年的艺术老人,与雏凤初鸣的小梅花团新人同时亮相,就构成了非常独特的风景。在我看来,这正是这个七十岁的剧院,迎来了自己的又一段青春岁月,也许就应该把这称作这个剧院七十岁的青春。
老艺术家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集体诗朗诵《我们的家》,一群老人用诗表达着对家的热爱、依恋、祝福和期望。他们所称的“家”就是他们处身的这个剧院,称之为“家”,是他们对这个艺术团体最深切的认同与依恋。他们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话,他们说,他们赞美夕阳,但他们更赞美朝霞;他们说,虽然只剩了一把老骨头,但只要这个家用得着,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奉献出来……。我想听到这样情真意切的内心表白,他们剧院的领导者们无疑会感到心里发热的,因为这质朴而自然的话语,是对剧院工作的最高评价和认知,也是对剧院领导者的最高赞扬与信赖。此前,我读到院长陈彦写的一篇感言,题为《敬畏•感恩》,他说:“作为剧院的后来人,我们不仅敬畏着革命前辈在炮火硝烟中的出生入死;也敬畏着艺术先贤在历史演进中的深厚积淀;更敬畏着他们善于继承,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进取精神。我们时常眼含泪水,那是因为这个剧院饱享了天地的恩泽。”这位年轻的院长誓言,“感恩前贤,感恩社会,感恩时代,我们将深怀敬重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承继历史,努力完成好我们应该完成的文化积累。”这则感言不长,但字字千钧,掷地有声,这可以视作治院方略,也可以看作庄严承诺。一诺千金,是我们民族自古以来的诺言认定,可敬的是,陈彦和他的同僚们,既把诺言化入了对大局的统领,又把诺言化入了行动的细节之中。就像我们注意到老艺术家这一次演出一结束,他们一帮领导就急火火地走上舞台毕恭毕敬献花一样,多年来,他们把“敬畏”和“感恩”的字样嵌入院训,把老一辈领军人物的形象塑在院中,把老一辈的赫赫业绩办成展览,让后来者时时刻刻沐浴在前人创造的春风化雨之中。而这一次的七十周年院庆,更是他们倾心倾力敬畏与感恩的一次集中体现。他们摒弃虚无主义,珍重前人成果,把七十年的秦腔名段编印成一套三大册的音乐经典,把七十年的演出剧照编印成一套瞬间永恒的画册,陈彦院长更是亲任主编,把七十年的研究文章编印成一套五卷的理论文荟,把七十年的优秀剧目编篡成一套十卷煌煌大观。在这个过程中,陈彦对剧院的光荣历史,优良传统、宝贵经验与蓬勃现状认真梳理,精心研判,写成了一篇《走过七十年》的厚重长文。这是一篇质美文华的难得的文字,对过去给予了全面的总结,对未来设定了明确的愿景。对于这个院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文化积累,既是对感恩与敬畏的演绎,又是对开拓与创新的揭橥。我于此感知了这个剧院能够持续保持上升势头的奥秘。
就像感慨老艺术家的演出一样,不能不提到小梅花秦腔团,这是由一百多名刚毕业的秦腔演员新近成立的剧院的第四个演出团体。几年来,陈彦院长一再强调要对这些孩子负责,五年的学习生涯,不只学戏学艺,更要学文化学知识,培养的是秦腔演员,居然连英语课也不让空缺,用陈彦的话来说,要培养的不是戏子、艺人,而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家,是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的传承人。这些孩子的毕业演出是青春版的秦腔《杨门女将》,一经出世,就不同凡响,不但轰动三秦,而且名噪京华。陈彦所说的对这百名学员负责,不仅包括了当年的培养方向,还包含了如今的使用方针,他说,这一百多名学员要一个不拉的留在院内,能演主角的演主角,演不了主角的演配角,演不了配角的跑龙套,跑不了幕前的做幕后,因为他们都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储备与艺术修养,做幕后的服务工作,也当会不辱使命的。在不少戏剧团体濒临解体困危的时候,这一百多名学员却成建制地正式组成一个演出团体,强势登上秦腔舞台,不能不说是一次异军突起。这不仅仅只是剧院的生力军,也应视作秦腔艺术的一支生力军,也是一支传承民族文化的生力军。这样一支生力军与已有的三个演出团的主将们主帅们合师,不正是构成了一个历经七十年沧桑,重新演绎风华正茂、光芒迸射的青春版的戏曲研究院吗?
一个牢记敬畏与感恩的人是让人敬畏的,一个牢记敬畏与感恩的团体,是会长胜不衰、青春永葆的,在我领略省戏曲研究院七十岁青春的时刻,突然就想起了宋人王令两句意味深长的诗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作者系陕西省作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