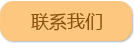李梅,11岁踏入戏曲界,12岁初登舞台,14岁担纲主演,30年来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功夫,唱念做打俱臻上乘。1994年由她主演的眉户现代戏《留下真情》,使她登上了戏剧“梅花奖”的领奖台,成为陕西第三位获得此殊荣的青年戏曲演员。1999年,由她主演的大型眉户现代剧《迟开的玫瑰》,在参加沈阳第六届中国戏剧节时,荣获“曹禺戏剧优秀剧目奖”;同年荣膺中宣部颁发的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并一举夺得了文化部设立的舞台艺术最高奖文华大奖和编剧、导演、作曲、表演四个单项奖,这是三秦戏曲史上的首次;同时还在陕西省建国50周年优秀剧剧目展演时,荣获了优秀剧目特等奖。
前前后后,李梅获得的国家级、省级大奖就有数十项。难怪连“老外”都夸她是“东方爱神”。
苦寒育得梅花香
刚刚踏进不惑之年的李梅,早已迈进艺术精英的门槛。国家一级演员,省政协委员,共青团十四大代表。从艺三十年来,获得过国家及省级无数大奖。
梅花香自苦寒来。李梅的今天却不是轻易走过来的。11岁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员训练班之初,学艺七年,主工花旦兼刀马旦,硬是练出一身文武兼备的扎实功夫,唱念做打俱臻上乘。12岁初次登台,13岁站在了舞台中央,14岁主演《杨七娘》,跃上了戏曲艺术征程的第一级台阶。其后,秦腔《鬼怨》及全本《西湖遗恨》,把她的表演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而1994年主演的眉户现代戏《留下真情》,更助她登上了戏剧“梅花奖”的领奖台,成为陕西第三位获此殊荣的青年戏曲演员。有的评论者把李梅这三出代表剧目视作她表演艺术的三级跳,颇有道理。而“一跃龙门”,却也并非易事。基于:
勤学苦练——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有一部艰难创业史,一部流汗、流血、流泪的艰苦奋斗史。李梅自在其中。
比如《鬼怨》,这出秦腔前辈艺术家的拿手好戏,要挣个“及格”已属不易,李梅却眼睛盯着“优秀”。于是,加倍地勤学苦练。她说:“想要戏够,脚下要溜。《鬼怨》全场,大多是慧娘在奔跑,飘忽不定,似影随风,要如同水上飘,不能摇摇晃晃,撒汤漏水,功夫全在腿上。为练好圆场,我绑起沙袋,沿着练功场,口中念着唱着,一跑就是几小时,同时练翻身,抛甩斗篷等等,每天下来汗水湿透衣衫,累得吃不下饭,甚至梦中都脚蹬手舞。直练到不酸不痛,虚肿消去,不昏不晕,才觉自如。”这“不酸不痛,虚肿消去,不昏不晕”的“自如”境界,包含了多少辛劳!多少付出!
贵在出新——一切有出息的戏剧演员,总不满足于照猫画虎地重复师长,“克隆”前辈。创新是一切文学艺术的生命,自然也是表演艺术家们的追求。李梅早年就为自己确立了这样的目标。
仍以《鬼怨》为例。这是一出唱做并重的重头戏,需要运用大段的唱腔和大幅度的身段动作来展示李慧娘内心的怨恨和悲愤。那出场前幕内的一声“苦哇”,在艺术处理上,李梅就着意于一种独特的追求。她运用脑鼻腔共鸣,辅以丹田之气,由弱到强,至强又趋微弱,音域上下超过两个八度,饱含着仇与恨,凝聚着凄凉悲怆之情,回肠荡气,撼人心魄,表现了冤魂飘忽不定,忽远忽近的游踪,渗透出一派凄厉肃杀的鬼气。又如圆场,李梅注意以身段的轻柔来展示慧娘幽怨的心绪。那柔缓轻盈如飘絮飞荡般的身姿,吸收了舞蹈的动静相若、急缓相协、张弛有致、开合有度的法则,于传统技法中透出新意,烘托出满腹幽怨的“这一个”多情而美丽的厉鬼。跑动中,洁白的披肩展幅加大,乘借奔驰腾挪的风势,加进转、翻、兜、抄等技法,以及水袖功中的抛撒收转、高抛低接、托挑甩打,时抖时落,时展时裹,更增添了艺术的美感。1995年石家庄举行的第十三届“梅花奖”颁奖晚会上,李梅的一出秦腔《鬼怨》,短短十五分钟,观众鼓掌竟达十四次。掌声是对演员辛勤劳动和精湛技艺的权威认定和最好回报。
玫瑰今又吐芳华
跨进“梅花”行列的李梅,艺术上并未止步,她坚守阵地,目不旁鹜,执着追求,从不流俗。在戏曲领地,辛勤耕耘,刻意进取。在大型眉户现代戏《迟开的玫瑰》中担纲主演,出色地塑造了感人至深的当代女青年乔雪梅的艺术形象。
一个风华正茂的女青年,憧憬着美好未来的中学毕业生,刚刚接到一所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突然祸从天降:母亲遇车祸身亡。剩下因工致残的父亲,三个尚未成年的弟妹。面对这天塌地陷般的打击,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她毅然放弃了上大学机会,心甘情愿地作出了自我牺牲。“要苦就苦我一个,不能让他们再作陪”。经过16年苦苦撑持,她先后三次舍弃了入学深造和成家立业的机会,把前途、事业和幸福让给了同胞弟妹和养妹,将身患残疾的父亲养老送终。直到36岁,才和暗恋她多年的下水道工人许师傅结为姻亲。
这就是《迟》剧中的女主人公乔雪梅。
不难看出,塑造这样的人物,不仅剧中人年龄跨度大,而且思想内涵与当今时髦的某种个人中心的价值观相悖;既难以表演,又还得顶着某些人高高举起的陈旧、保守、落伍的不大不小的帽子;艺术上、精神上都不能不说是一场挑战。
李梅挺身应战了。她以出色的技艺,塑造了活鲜鲜的“大姐妈妈”的艺术形象;以她的一片真情,感动了最前卫的青年观众——高等学府的师生们,得到了他们广泛的认同;更以剧中人纯洁高尚的内心世界以及传统美德的芬芳,给了人们以心灵的震撼。
在乔雪梅形象的塑造上,李梅调动了积累,发挥了优势,加强了吸纳,付出了心智。我以为,有这样一些努力值得注意:
一是把准人物的基调。这是塑造好人物的前提。李梅说:“乔雪梅这一艺术形象是全新的,不同于旧戏里的三娘、秦香莲,也不同于《渴望》里的刘慧芳,她是自己的‘这一个’,即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基于这样的认识,剧中,李梅没有去着意渲染雪梅的凄苦与无奈,而是展示她理智的自主与抉择;不去呼唤怜悯与同情,而是引发崇敬与理解;不是怨天怨地,萎萎缩缩,而是自强不息,有所作为。这就保持了积极向上的昂扬,避开了悲悲戚戚的低沉。为了表现好这一点,李梅从一出场就注意了人物的特殊身份:集才貌于一身的女中学生、俊美的“校花”,她有理想,有追求,有幸福的萌芽状态的恋情,也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定下了基调。而一旦严酷的家庭变故降临之后,在一次次地奉献、忍让、牺牲的抉择中,则努力揭示其内心斗争,揭示其不得不如此的内心依据;特别是面对善意的同情及不那么善意的悲悯甚至奚落,更着力展示她寻求心理平衡的痛苦抗争,那些“天问”式的求索追寻……这一切,都让人们看到了雪梅作为新型女性的丰盈的内心世界,加深了对她的理解及崇敬之情。当雪梅昔日的恋人,如今的副市长温欣转达了同学们对她人格的“崇高”评价,并感慨于当年没有年龄感、没有历史感、没有责任感而小看了雪梅的价值,感慨于“整整十六年才读懂一个人,真是太残酷了”之时,我们,舞台下的观众,能不感到心灵的震颤!
二是把准人物的跨越。全剧长达十六年的时间跨越,给表演者添加了难度,但也给了展示表演才华的机会。对于主人公乔雪梅来说,这个跨越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自然年龄意义上的从意气风发的少女跨到成熟沉稳的中年女性。二是职业身份上的从天真无忧的女中学生跨进到上管老爹下管弟妹的操心柴米油盐的当家人、家庭主妇。李梅出色地完成了女主人公的这种跨越。从衣着,到步履,从神情,到心理,可谓自然熨帖,顺理成章,不事张扬,却又步步到位,观众于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种跨越,认同了这番嬗进。特别是第二场,雪梅从富于幻想的校园生活陷入日常琐细的家务漩涡里,柴米油盐,养家糊口,事事操持,件件烦心。李梅一路演来,惟妙惟肖。算账、摘菜、喃喃自语诉说与商贩讨价还价的情景,那一套家庭主妇操持家务特有的习惯动作,以及因为丢失一元钱则心神不宁的神情,李梅演来真个入木三分。
三是把准心路的层次。乔雪梅不是高大全的英雄,并不天然具备应付多种突发事件的本领,家庭变故是在她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发的。从“我要上大学!”的呼唤,到找准“大姐妈妈”的感觉,再到审视十六年“挑夫”生涯的无怨无悔,乔雪梅一步步完成了心路历程的攀升和思想境界的完美。李梅在塑造乔雪梅形象的时候,十分清晰地把握了这由被动到主动,由不自觉到完全自觉的升华,将其层次分明地展现了出来,构成了高尚寓于平凡,可钦更觉可亲的全景式的生活画面。
四是把准表演的风格。《迟》剧写的是大城市深巷小院中发生的凡人小事,乔雪梅只是个中学毕业顶替母亲进厂做工的普通工人,并无引人瞩目的业绩,也无惊世骇俗的壮举。李梅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有意识地选择了真实、真切、真情的路子,自然流露,朴实无华,不事雕琢。除了对付弟弟因失恋而失态,曾击一猛掌之外,雪梅自始至终几乎没有大的形体动作。内心的风暴雷霆,化作“好着哩”的泰然平静;柔弱纤细的身躯,承载着物质的、精神的、生活的、舆论的千钧重负,却又都在默默无语中扛起,推进。没有暴风骤雨的剑拔弩张,情感却渲染得十分浓烈。个中的诀窍,我看得力于眼睛的运用。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李梅很会用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顺次说来,毕业烛光晚会上那双熠熠闪光的眼睛,充满青春气息和美好憧憬;母亲死于车祸,家庭突遭变故,严酷打击下的眼里充溢着惊诧和失落;盘算着菜贱肉贵的女主人公,眼里光泽淡去,只剩下几丝木然和迟疑;责打弟弟,眼里流露出“大姐妈妈”的“恨铁不成钢”的诘难;应付姨妈的好心提亲,眼里是凄然无奈;面对同龄人的成就,则是疑虑、焦急、探究的目光;弟妹事业有成,迟开的玫瑰芬芳,让她眼里重新闪烁着光彩,那已经是自信的成熟的光灿了。统观全剧,李梅确实用眼睛告诉了人们许多许多。
秦腔琴韵吐清奋
戏曲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运用唱腔塑造舞台人物,音乐堪称戏曲艺术的灵魂。因而,演唱艺术对于一个戏曲演员来说,既是合格与否的起码要求,又是造诣高低的检验标尺。李梅可以说是一个很善于用“声”的人。她的嗓音条件在勤奋练习的基础上已转为强项,更加上演唱技法上的博采广纳,融会贯通,在继承秦腔传统中迈开新步,唱出新音,攀上新高,成为秦腔演员中的佼佼者。
李梅演唱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善于声情结合,以情用声。二是运用科学发声方法与技巧,丰富其音乐形象。李梅通过《迟》剧塑造的音乐形象,充分展示了她的演唱才能,也标志着迈上了声乐艺术的新台阶,成为新一代秦腔旦角艺术的代表人物。
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在太多诱惑的年代,年轻的从艺人难得还呆在戏剧舞台上。李梅在地方剧数十年不从流俗,酷爱秦腔,苦学苦练,终于在不易走红的戏剧舞台上走红。应有赞联:萤飞光自照,梅雨色不褪。”深同此感,仿之,送贺联:暗香袭人缘霜重,傲雪红梅色更妍。
(作者系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文艺评论家)